男女主角分别是李烨符存的现代都市小说《太宗之后,再造大唐李烨符存前文+后续》,由网络作家“理振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人各有心思,却是一同摆了香案,面朝远处数里外,高耸矗立的太宗李世民陵寝。虽然大唐已经过去两百多年,自安史之乱后,国家纷扰,朝廷动乱,尤其是宪宗以后,几个皇帝要么是太监傀儡,要么沉迷享乐,早不复天子威仪。各地封疆大吏和节度使们,虽然大多依旧还遵从朝廷诏命,但心中早已不把什么“天家威仪”当回事。待到黄巢之乱后,朝廷更是只能和周天子一较高下了。但太宗文皇帝的声誉,在民间依旧不可动摇所谓“孤忠无路哭昭陵”,可以说直到现在,军事力量实际已经不足以威慑藩镇的朝廷,还能勉强支撑,很大程度上,都是依靠这昭陵里那位皇帝,留下的巨大政治声誉遗产,让人心尚存唐室。正因如此,虽说各地藩镇早不服管束,但作乱还大多只为了兵将私利,没人真的敢自立为帝,否则必成众...
《太宗之后,再造大唐李烨符存前文+后续》精彩片段
人各有心思,却是一同摆了香案,面朝远处数里外,高耸矗立的太宗李世民陵寝。
虽然大唐已经过去两百多年,自安史之乱后,国家纷扰,朝廷动乱,尤其是宪宗以后,几个皇帝要么是太监傀儡,要么沉迷享乐,早不复天子威仪。
各地封疆大吏和节度使们,虽然大多依旧还遵从朝廷诏命,但心中早已不把什么“天家威仪”当回事。待到黄巢之乱后,朝廷更是只能和周天子一较高下了。
但太宗文皇帝的声誉,在民间依旧不可动摇
所谓“孤忠无路哭昭陵”,可以说直到现在,军事力量实际已经不足以威慑藩镇的朝廷,还能勉强支撑,很大程度上,都是依靠这昭陵里那位皇帝,留下的巨大政治声誉遗产,让人心尚存唐室。
正因如此,虽说各地藩镇早不服管束,但作乱还大多只为了兵将私利,没人真的敢自立为帝,否则必成众矢之的,如的德宗朝“二帝四王”之乱,敢称帝的那位连全尸都找不到了。
可太宗这杆大旗,又能庇护腐朽的大唐王朝几天呢?
李业、符存审、杨师厚三人,按照齿序年龄,以符存审为长、李业次之、杨师厚再次。
面朝昭陵,恭拜而跪
三人之间,虽然因年龄以符存审为长兄,但实际上,隐约以李业为首。
盖因无论是联络张承业,还是杀人后投奔西北,大多都是李业拿的主意,其余二人对其眼界智虑颇为叹服,虽说以眼下李业的身份地位,二人还不至于以从属自居,更多只是合作,但在大事上,比较听从李业建议。
尤其还是在昭陵之前,李业这个宗室之后的身份更显作用
故而李业率先起誓
“太宗文皇帝神灵殷鉴”
“不肖子李业,系高祖十世孙,太宗九世孙,愚陋寡能,不能扶社稷,安黎庶,以尊祖宗基业,今诛杀阉竖,出奔河南,意在效命戎武,安定国家!”
“得同志兄弟,义谱金兰,勠力同心,共赴国危,以上报宗庙,下救百姓!”
“故立此誓,即为异姓兄弟,吉凶相济,患难相扶,利同泽,危同担!生死相依,共扶社稷,绝无二志!”
“皇天后土,祖宗神灵,我太宗文皇帝殷鉴之!”
“如违此誓,万夫所指,天人共戮,死无全尸!”
随后,符存审、杨师厚接着起誓
誓罢,三人抽出短刀,面朝昭陵,歃血为盟
随后相互作揖,互称兄弟,便是礼成。
秋日天高云淡,更显九嵕山,虎踞渭北,一峰独秀,宛若一个巨人端坐在位,俯视着这一幕。(bgm:这一拜~春风得意遇知音~~)
此时的三人,其实说不上多少雄心壮志,一则出于以后共同打拼,相互扶持的需要,二则出于之前一同杀人逃命的义气友谊。
但此后真的风云际会,勒名青史,就是后话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广明元年春,夏州,德静县外
“嗖!”
一箭飞矢,正中马首
战马中箭哀嚎,足下失措
马上党项首领顿时倾倒,身侧二十多名党项步卒,见首领扑地,顿生慌乱。
其余游骑仓促之下,未及反应
符存审见状拔刀,厉声高呼
“冲!”
数十步骑,皆披甲执刃,结阵冲上
李业亲自带着十余骑兵,以骑弓继续追击剩下的党项游骑
至于步兵,就交给符、杨二人。
而杨师厚则带着射程更远的步弓和弩手在后
唐军相较于党项、回鹘诸部,能以少击多,关键就在于兵锐甲坚,阵型严谨。
一百四十名由骑兵、披甲步卒、弓弩手组成的阵列,顷刻间就把群龙无首的党项人冲得七零八落。
白刃纷纷,双方骑兵穿梭于战场,李业手中强弓,能达一石五斗,五十步内,贯甲而出,勒马回身,抬手张弓,便又是一骑落地。
这大半年来,他最大的长进,就是在符存审帮助下,精进了骑术
“陌刀,前驱!”
李业勒马来到步兵阵列最前,振臂高呼
随后以符存审为首的十名,队伍中最身姿最健士卒,从身后取下齐头高的陌刀,随即合并成列
刀锋向前,步步推进
其余将士持步槊、横刀在后,弓弩手居两侧,骑兵跟着李业游荡在外
李业一边策马,一边左右发弓
“嗖嗖”
刁钻的倒刺箭头,如同毒蛇,不断吞噬生命
而唐兵的步兵队列最前方,陌刀阵宛若压路机一般,在缺乏甲胄的党项步骑之间,留下一道血痕。
符存审手擎长刃陌刀,看着快速逼近的党项骑兵丝毫不惧,咧嘴一笑
“开!”
“砰”
只见锋刃划过,那骑士被整个劈下马来。只是其人居然着甲,可能是个小头目,流血不止。却未当场身死,但还没来得及惨叫,就被符存审身后士卒用横刀补伤,斩下头颅。
所过之处,人马俱碎
身后将士的步槊、横刀,负责把被陌刀阵冲散的党项人一一包围擒杀。
一百多党项步骑,就这样在不到两刻钟时间内,尸横遍野,仅剩下二十几个俘虏。
看着已过正午的阳光,李业翻身下马,摘下头盔
对杨师厚道
“三弟,安排人赶紧搜检缴获吧,咱们这次离军堡太远,逗留久的话,唯恐路上被党项人截杀。”
杨师厚称是
紧接着,清点完斩首、俘虏的符存审前来报告
“副将,都点完了,斩首七十有四,俘虏二十八人,还有几个游骑逃脱了,没追上。”
虽然按年龄,符存审才是三兄弟中的老大,但如今李业职务为副将,而符存审和杨师厚都只是队正,所以二人都要执下官礼。
(注:唐末五代藩镇军职等级为:火长—队正—十将—军使,一火十人,一队五火,十将所辖若干队,称为一都。每级军官各有副职,李业的副将,便是十将之副,若干都合为一军,长官为军使,军使再往上,就是防御使、节度使等藩镇头子。当然,军使本身也可以成为小军阀,不一定要归属某个节度使管辖。)
对此,其实符存审也没有太多愤懑,除了一开始时有些心中不愉,但李业并没有因此而怠慢与他,也就看开了。
归根到底,还是符存审本人的性格豪爽,非小肚鸡肠,而李业能耐也的确能让他认同而已。
李业也是上前握住符存审的手,爽朗笑道
“大哥,此番斩首颇丰,等回去得了赏赐,自当痛饮一番!”
自从来到这长城之外的边戎之地打拼,李业就愈加庆幸于自己拉拢了这两个义兄弟。
军队,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军队,最讲拉帮结派,没有自己的几个嫡系能用。
别说爬上去,当个队正都够呛。
二人又议论了番具体斩获,斩首里有两个党项酋长,按照之前节度使诸葛爽开的赏格,应有二十匹绢。
紧接着没过多久,杨师厚就过来汇报缴获
党项人装备简陋,所以除了这些贼人随身携带的抢掠来的财货外,只有长矛、刀剑、软弓一类,以及八匹战马。
皮甲不过二十几副,铁甲仅有四副
按照军纪,这些东西都是要押回军堡归公,然后再分配下来,但李业哪里会有这么老实?
虽说他所在的德静县,驻有一都,十队五百余军士,他是副将,同时也兼任一队队正。五百人中,真正属于自己嫡系的,却只有自己所辖一队和两个义兄弟的人马,合计一百五十人。
所以李业当然要想方设法,把自己的嫡系武装起来
杨师厚得了李业示意,带着亲信,把铁甲和几副质量上佳的皮甲、弓箭、横刀,从战利品里分出,等回城时埋在军堡外,过段时间再取出。
至于战马,也要挑出四匹气色、体格最佳,没受伤的留下,其余带伤的才上缴。
之所以这么做,也是因为十将王贺与李业之间素有不对付,这些天不少刁难。
李业三兄弟来到夏绥镇已经半年
说起来这半年的际遇也是丰富,一开始他们在河南拜访诸葛爽,原以为自己出身微末,就算有张承业的介绍信,恐怕也就是从基层干起。
没想到诸葛爽看过张承业书信后,却是大喜过望
把三人全部安排到自己亲兵都中,任为队副
这倒不是因为张承业和他干爹张泰有多大脸面,这时候,虽然京畿之内,是太监们一手遮天,但一出长安,到了地方藩镇上,宦官们的脸面虽也要顾及,却也没多大效用了。(当然,如三川、淮南等直属朝廷的藩镇除外)
而是诸葛爽此时正在讨伐李国昌、李克用父子叛乱,朝廷升他为行营副帅,可以统辖周边兵马,但他刚刚履任不久,急需培植亲信。
这年头当军阀、节度使,可是个高危职业
残唐五代,虽然同样轰轰烈烈,却和相似的汉末三国不一样
最大的特点,就是道德败坏,上下、君臣,全无信义可言。
简单来说,就是人均三姓家奴,个个骄兵悍将。如赵匡胤黄袍加身,欺负孤儿寡母,在五代,真的算是道德高尚了,起码没有斩尽杀绝,给老主家一个体面。
在这个时代,节帅篡位,将领杀帅,军官杀将,士兵杀军官,取而代之,屠人满门,淫人妻女,甚至把人尸体分予众人分食,简直不要太寻常。
所谓“长安天子,魏博牙兵”,闹得厉害的如魏博镇这种,牙兵们都不把节度使当回事,反倒是节度使得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,生怕哪天被人砍了。
诸葛爽初到任上,并不意味着手下的骄兵悍将就会听他的,所以正需要加强亲信嫡系。
而李业三人,既有本事,关键还没有根基,与本地诸将都无关联,简直就是天然可以收为己用,给军中掺沙子的人才啊。
果然,诸葛爽把三人留在身边,当了两个月的牙兵队副,参与到平叛过程中。
在此战里,李业三人其实没有经历什么恶战,因为李国昌父子很快就又被招安了。
而诸葛爽则因为平叛有功,升为夏绥节度使。
接着便以节度使调令,把三人升为夏州北面,德静县军堡,任队正。
后来李业在德静追缴党项马贼有功,又以此提拔李业为副将
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德静为夏州北面门户,这就是在趁机伸手收拢掌握地方军权。
但这显然就得罪了作为地头蛇,于德静盘踞已久的十将王贺
“好!就依孟仆射之计行事!”
一日后,黄巢“仓皇”东逃,车马仪仗扔了满街,部署甲士纷纷护从,慌乱得紧,城中幸存的大户豪族,无不喜极而泣,似乎浩劫马上就要到头了。
三日后,凤翔唐军前锋抵达长安,获知了黄巢已经逃窜的事实。
路上除了一些零星乱兵,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
三军欢呼,自金光、开远二门入城,残余的世族,甚至出城相迎,恭迎凯旋......
就连原本因为李业的提醒,而略有担忧的郑畋,听到消息也放下心来。
似乎,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李业本是不愿意进入长安城的
当然,其余各军也巴不得少一个分羹的人,毕竟此时的李业,也是一支一千两百人的独立将领(原部三百,郑洵带来的另外近千夏绥镇兵马,在编为凤翔镇衙军后,也归李业统带。)
但随着程宗楚和唐宏夫率军成功进入长安,且并未遇到任何抵抗
原本有些担心的许多将领,也彻底放松下来
就连郑畋本人,也打消了最后疑虑,对于这位老人而言,收复长安,也是他拼命实现的目标,能获此殊勋,谁能够无动于衷呢?
再说,就眼下而言,长安的确就在唐军手中,巢军的确已经退出了长安。
于是乎,郑畋也开始往长安而来
这下即使李业不愿,也不得不来长安了。
时隔一年半,李业再次勒马行在长安街上
二此时的长安,与他印象中那个,已然大不相同
其实黄巢初入长安,军纪还是不错的,他本人也许不是善良之辈,但确是野心勃勃之人,既然要代唐自立,自然要尽可能树立自身形象,故而除了宗室贵胄和豪门大族外,并没有对其他人动手。
只是,显然黄巢对于自己部属的控制力,还远没有达到李业这种水准。连李业都得依靠立威才能把部属管束,何况黄巢?
虽然限于明令,没有发生大的掳掠,但许多中产、小富之家还是遭了殃。
东西两市随之萧条,只有各坊内的街市,勉强还有几分烟火气
李业和符存审、杨师厚,专门回了一趟以往住处。
自己那套院子,居然还在,大概是杀了董五后,被他小弟什么的占了,但其中人早已逃难。
随即李业好奇打听了董余的下落,得知这位昔日长安城里的奢遮人物,原来早就死在了潼关,田令孜可以跑路,却没有他这个神策军判官的份。
至于张承业,倒是成功跟着自己义父,随驾逃亡蜀中。
三兄弟勒马于朱雀大道上,看着远处依稀可见的太极宫和大明宫巍峨宫阙
李业却是问道
“弟兄们没有进内城吧?”
杨师厚回答
“没有,都在延平门那边等着呢。”
此时程、唐两部主力都打着肃清巢贼余孽的旗号,往着皇城方向去了,但李业却把自己士卒约束在了外城。
当然,所谓恩威并施,也不能一味靠刑法威慑。
李业既然到了长安,就没有部分一口汤的道理,只是相较于那些往皇城而去的友军
他选择先带兵围了城南诸坊,然后开始做和黄巢军一样的事情
吃大户
要求宣义、率安等十坊凡上户以上的富家,每户出绢两匹到十匹不等,或钱三贯以上。
黄巢第一波清理的,主要是豪门大族,且也没有清理干净,一半都不到,城中虽然萧条,但富家仍然不少。历史上真正的浩劫才刚刚开始。
同时,这位老相公,站到了战场最高处,亲自擂鼓助战
午后阳光,开始一点点向西面推移
时间惊心动魄地流逝不断
终于,忽然,一声欢呼,不知是从哪个军士口中发出,紧接着就此起彼伏,席卷整个塬上。
所有唐军士气忽然大振,塬下巢军完全没有弄懂发生了什么。
因为只有塬上可以看得清楚,距离战场数里之外,一面面纹绣着各式字样的旌旗,正不断从地平线下涌出。
其中最明显的两面,上书“程”、“唐”二字
援军抵达了!
战场前沿的巢军本就处于高伤亡的紧张状态,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,待后面的喧哗声越来越大,才逐渐明白发生了何事。
巢军中军的精锐甲士,此时已经被抽调一空,就算剩下三万多士卒,可大多乌合之众。
程宗楚、唐弘夫两万步骑精锐,犹如下山猛虎,突然从龙尾坡两侧杀出
对方中军,连半个时辰都坚持不住,迅速就转为全面溃败
而崩塌的士气,就像森林火灾一般,飞速洗染全军,很快就把连锁反应传导到了前方军士。
而塬顶唐军则是士气大振,纷纷结阵往下冲击,两相夹攻之下,巢军迅速进入总崩溃。
奔逃的士卒满山满野,丢盔弃甲,身后追杀的唐军步骑穷追不舍,所到之处,留下遍地尸首。
此情此景,和一个多月前,潼关所发生的事情,几乎一模一样。
尚让几乎是看到侧后方唐军出现的那一瞬间,就立马带着近千亲卫骑兵,和主要将领拔腿跑路。
朝着东面长安方向狂奔
这倒不是说尚让怕死,只是作为转战全国的义军老人,他对这种情况简直太过熟悉,军队只要一开始崩溃,就不可能拦得住,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带着亲信抽身。
果然,他的预料是正确的
一支军队,想要训练成能参战的整体,要花不少钱帛、心血,但一旦崩溃,不过就是眨眼的功夫。
李业见对方原本紧逼的精锐甲士,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,当即大呼
“援军已至,草贼已溃,众将士随我立功!”
随即率先冲入敌阵
而塬顶一直在击鼓助威,同时也在观战的郑畋也已经反应了过来
干脆弃了鼓槌,直接亲自翻身上马,高喊催动全军追击。
李业和符存审也各自上马,带动甲士衔尾追杀
被之前巢军大举压迫,所造成的恐慌,导致紧张异常的唐军将士,忽然得此胜利,宛若疯狂的朝着溃败的敌军冲击。
那数以万计,深色恐慌的人群,都是他们眼里的战功
程宗楚、唐弘夫以逸待劳的两万步骑,宛如两柄钢刀,所过之处,血流成河。
残尸断刃,满坑满谷
唐军无暇顾及什么俘虏,几乎是见人就杀,尤其是在密集军阵的兵锋之下,只要没有主将命令有意图的接纳俘虏,那前方溃逃的散兵就只有一个结局。
全军追奔近十里后,郑畋才下达了除骑兵外停止追击,同时搜捕俘虏的命令。
只是,此时唐军各部还能听进去多少,就是另说了。
但至少李业部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
他立即宣布停止追杀,并让各级军官传达,表明俘虏和斩首同功。
这才勉强约束住下面的军士
随之而来的,是大量倒戈弃甲而降的巢军士卒,本来他们就已经陷入崩溃,突然遇到一支愿意纳降的唐军,也就成片投降起来。
此战之后,李业部五队将士,伤亡数十人,李业组织人把阵亡遗体埋葬在石子岭,并举办军葬。而难以行动的伤员,则被安置在后方由驮马组装的板车上。
至于赏赐,李业和军士立法三章,此后无论有多少人,但凡发放赏赐财货,都必须在全都至少一半,数百人众目睽睽下,把其人功绩宣读,而后当场清点发放。若有异议,可以当场质询,队正、副将等军官但有贪墨,值一贯以上,枭首悬头于门!
但同样的,若是宣读公示,清点查收以后,就不得再无端生事,擅自鼓动闹饷,违者,和军官贪墨一样,枭首悬于军门。
事实上,李业为了坚持自己的诸多规矩和原则,也导致了很多反面后果。
比如从德静时,就有不止一个受不了管束的老兵,离队转投其他军头。
这也导致李业部在诸军当中,显得格格不入。之前诸葛爽在众将面前,赞赏李业,就引起了不少人嫉妒抨击。而李业本人,在夏绥军中,也的确比较孤立。
但李业并不后悔
一支军队的灵魂,在于纪律,法纪这种东西,如果一开始不严肃对待。那之后,再想树立起来,就难如登天了。
否则,就算自己有百万大军,能横行天下,一朝出事,马上有人“黄袍加身”,或者落个李存勖那般下场,再大的功业,又有何用?
处理完军中事务,李业并没有闲下来,而是立马去拜访之前分发各部赏赐的节度判官,郑洵。
郑洵是名门之后,荥阳郑氏,从几百年前就是世家豪族,五姓七望之一,当过宰相的族人,得上两位数。
纵然不是嫡系,但就这出身,就属于统治阶层上层行列。
虽然到了唐末,世家大族的地位今非昔比,地方军阀和朝中太监,早已越来不把他们当回事。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,这些人在本地和朝廷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。
尤其是关中,各个富庶州县的主官,都还是这些大家族掌控。
而李业拜访的目的,就是想要打听一下朝中消息。
不同于这时代大多数武夫,李业知道,还有不到一年,黄巢就会攻破长安,虽然由于不清楚历史细节,他无法获知黄巢是怎么打到长安的,毕竟直到现在,黄巢都还在江南活动,距离长安几千里呢。
但他清晰的明白,黄巢之乱,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机会。自己想要就此登上历史舞台,成为未来可以和李克用、朱温、杨行密、耶律阿保机等乱世枭雄博弈的大佬的话,就必须尽可能利用这一时机,发展壮大自己。
“子烨多礼了!”
节帅大帐之侧,是诸多幕府属官和幕僚的驻地
郑洵见到李业拜访,还带着礼物,倒是没有太吃惊
这位年轻的将佐行事风格不同于一般军头,彬彬有礼,颇有读书人士风,他之前在夏州时就有见识。
若是寻常武夫,倒也惊奇,但考虑到听闻其人乃宗室之后,倒也理所应当。
郑洵今年已三十有六,四年前考中进士,在尚书省为郎一年后,分派到关中藩镇。
其实也是带着家族任务,希望和藩镇武夫打好关系,以备不时。毕竟世家大族们也知道,这时代有刀把子才是爷,故而唐末以来,他们也积极寻求和兵头军阀们合作。
“末将参见判官!”
节度判官理论上是藩镇三号人物,相当于朝廷里的宰相,只是不掌兵权,没人当回事罢了。
但李业还是一板一眼的表示尊重,执下官礼
郑洵十分满意,连忙扶起对方
“诶,子烨宗室之后,血脉尊崇,又是功臣,我焉能受礼啊?”
“子烨举止文雅,有士子之风,日后称一声表字便是”
从其人言语便能看出,在这些世家子眼里,评判人高低的首位因素,还是出身家族。
二人坐在马扎上寒暄几句,李业便切入主题
“美江兄,我开拔后,在银州那边同僚听闻,说黄逆已经攻破江南,可有其事?”
这些世家大族,子弟广布全国为官,消息要灵通得多
“确有其事。”
“上旬长安邸报,说是草贼已破扬州,恐怕江东诸道,未能幸免啊”
郑洵感叹到,夏绥镇距离关中不远,故而时时都能收到长安的消息。
“不过毕竟还是危及江南,草贼既已破了淮南镇,想必师老兵疲,难以再兴大军,一两载内,南图中原,离我关中西北还远呢。”
不仅是郑洵,事实上此时天下大多数人,虽然都能看出黄巢攻破江南,对唐廷是致命一击,直接断绝了朝廷小半财赋供应。
但却没有几人能够遇见到,现在还在江南的黄巢,居然会在未来短短半年内,就兵抵长安。
就连李业本人,只是知道后世历史,黄巢的的确确是在广明元年后杀进了长安,由于黄巢起义是中学历史必讲的,李业记忆尤深。可现在这个样子,都已经广明元年了,黄巢离关中还隔着好几个省呢!
李业有些疑惑
但作为后世人,置身事外的看待历史,总是能比这时候大多数聪明人清楚,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
他似乎想到了一些可能
继续问道
“美江兄可知,如今在淮北主持大局,应对草贼的,是何人物?”
“乃门下侍郎,弘文馆大学士,宰相卢携”
郑洵答道
“不知这位卢侍郎勋纪如何?”
勋纪就是战功,意思是卢携有过啥军事战绩,李业倒没有因为人家是文官而看轻,大唐能打的文官很多。
谁知郑洵答道
“卢相公四代名臣,士门之后,家风蔚然,气节骨梗。”
嗯,就是没打过仗的意思。
李业又问到
“那眼下江北还有哪些得力藩镇?”
“忠武、宣武、天平诸军尚在淮北,魏博、昭义、平卢亦是强藩,相必不至于让草贼流毒中原。”
听到这里,李业已经明白黄巢是怎么从江南一路杀到长安的了。
郑洵说的这些藩镇,不是没有强军,有些甚至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精兵。
但,都是墙头草
以前唐廷有江南财赋在手,还能以财货诱其卖力。
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江南已经完蛋
那问题来了,人家为啥帮你平叛呢?
这些人自己没变成叛军,就已经很对得起你老李家了!
淮北中原,真正能用的,其实就只剩下高骈剩下的三瓜两枣,和河南东都的神策守军罢了。
除非能有个张巡、郭子仪之类人物坐镇,或者把高骈提溜到北面来当主帅,或许还有一两分胜算,而目前主持局势的卢携又不通军事。
结局已然注定
对于李业的询问,郑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,宗室嘛,关心一下国家大事也正常。
接着就笑问李业
“子烨此番立下大功,既已经升了十将,按常例,就可以加授本官了,愚兄在尚书省有些门路,需不需要帮忙活动一番?”
李业知道对方在示好,只是他心中真的不把这些虚名当回事,不如几十柄陌刀、弓马管用。
但人家都主动到这个份上了,自然不能拒绝
“就有劳美江兄了,事后必有重谢!”
郑洵只觉得这位年轻的宗室小将真是上道,满意笑了笑
二人又闲谈几句,李业才告辞离去。
不同于郑洵的轻松,李业掀开帐幕之后,笑脸就收敛了起来。
果然,黄巢入长安的历史潮流必然发生。
而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,现在已经是广明元年五月,最多只剩下大半年。
自己该如何应对?
一方面,要火中取栗,趁机捞足政治和军事资本。另一方面,又要保全自身,不至于变成藩镇和黄巢军倾轧时的牺牲品。
最好的办法,就是找一个距离关中、长安足够近,能随时动作,但又不被战火波及的地方落脚经营。
李业把目光投向了西面
三日后,大军与突围的经略军陈武韬会合,再次启程,往盐州方向而去,途经宥州
而在这里,李业第一次见到后世历史书上,与契丹、赵宋、完颜争衡,立国西北的西夏李氏
兴业之祖,拓跋思恭。
一旁旁观良久的李振、敬翔二人,见状也是心中思虑良多
敬翔不禁侧身对好友低声叹道
“此子,有王霸之才!”
李业到底有无王霸之才暂且不论,但咸阳桥战后,效节军一下子,就变成了长安以西,整个关中西北部最有战力的藩镇势力。
虽然此时,战后清点完伤亡,效节军仅有两千八百多能战军士。
可李业坚信,此时的两千八百多人,反而比之前那三千五战力更强。
至于人数,扩编就是了!
反正黄揆死了以后,黄巢在东边的主力,黄邺、朱温等人没有回援之前,都是没法染指京西的。
李业有大把的时间兼并地盘,扩充队伍。
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控制咸阳一地了,倒不是贪心,而是因为既然要扩军,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地盘来养。
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,黄巢入长安后,与唐军之间的战争先后延绵长达三年
这才半年都没过去呢,持久战还在后面,必须先找一个落脚地。
于是乎他派遣敬翔、李振,前往奉天(今乾县)、醴泉(礼泉)接管府库衙门,当然,他的图谋不止于此三县,而是北面的邠州,邠州作为邠宁镇的核心州府,又在京畿之侧,是相当富庶的。而程宗楚、唐弘夫死了以后,邠宁、泾原两镇节度出缺,邠州局势混乱,只剩少量残兵驻守。
不过此时,李业又深感自己手中人才不够用,武将虽多,但能帮忙打理地方政务,钱帛粮草,征收捐派,又能稳定人心,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地方豪族,和升斗小吏的经济之才,却太少了。
得到两敬翔、李振,就按着往死里用,二人现在都是身兼数职,当然李业也不亏待,工资也发几份的。
而现在,原先一县之地马上就要扩张数倍
于是乎,李业就在西逃聚集于咸阳的长安士民,和本地士民间张贴告示,表示临时聘用二十名文员,用以参赞庶务,虽然暂时没有官职,但俸禄照发,甚至有奖金,并且只要表现合格,可以上报朝廷补发告身。
有了这二十人,加上部分留下还没跑路的本地官吏,基本也就够用了。
这事,当然还得敬翔、李振负责,最后只得让李振先去醴泉接管衙门,敬翔留下招人。
没成想,这告示才张出去没多久,就有大鱼上钩了。
“韦庄?”
李业从敬翔口中听到这个名字,先是有些楞,然后反应过来,这不写诗的那位嘛,《秦妇吟》,就“天街踏尽公卿骨,内库烧成锦绣灰”这句诗的出处,就是人家写的。
印象中,其人好像在五代十国当过宰相(其实是前蜀政权的丞相),既如此,应该还是有本事的。
于是就向敬翔问道
“你试过了?能力如何?可堪大用?”
李业招人当然不是啥歪瓜裂枣都要的,他让敬翔临时出了些题,当然不是诗词歌赋啥的,又不是科举,就考些数算,钱粮载计的功夫,以及一些常见庶务,能写公文告示。
答出来再面试后,就可以用了。
但敬翔却是摇头,问道
“将军真不知韦庄是何人?”
李业有些疑惑,莫非此时的韦庄,已经是有名的大诗人了?
当然不是啦,敬翔见李业是真不知道,就解释
“将军可闻长安民间有谚语,‘城南韦杜、去天尺五’,韦氏自汉代起,就世居京兆,汉时便有三世三公,到了我朝,前后共出宰相一十七人!”
匆忙数天时间,凑齐的“十万大军”,终于离开长安,向潼关方向挺进。
圣人亲自出城为大军饯行
这位曾经做出“马球定三川”荒唐之举的天子,并非是不聪慧,只是大都多用在享乐罢了。
面对汹汹而来的黄巢义军,年轻的皇帝也慌了神,六神无主之下,只有紧紧抓住亲信的“阿父”田令孜。
当田令孜拍胸向他承诺,还是勉强稍安定下来。
他对战争没有直观概念,只是觉得京中神策军好歹十几万人呢,就算拖不住,也够护送自己跑路吧?
大不了再回蜀中高乐便是。
而这一日,送行的却不止皇帝
无数士兵家属挤在咸阳桥边,哭声震天,士卒们同样是心情戚悲
母子、夫妇,抱头掩泣,依依难舍
他们哪里是什么职业军士?就在前几天,还是东西坊挑货的力夫,走街串巷的货郎、巡道的衙役、门店里的伙计。
还有商贩、赘婿、游侠......
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
耶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。
牵衣顿足拦道哭,哭声直上干云霄!
距离城外不远,长安郊区的一处酒肆上
两名文士打扮的年轻人在二楼,斟酒对饮,遥遥望着这一幕。
其中一人苦笑道
“若非和右军的支计官有点旧识,此番愚弟恐怕也难免这一遭啊。”
对面人嘲笑
“什么旧识,不就是贿赂吗?亏你也是名臣之后!”
二人,一个姓氏很少见,唤作敬翔,冯翊人(三辅,长安郊区),昔日唐中宗朝宰相敬晖之后,两年前赶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,未中,就一直留在了京中。
而另一位年纪稍长,身世就更为坎坷些,虽然祖上也出过节度使,但在关中豪门大族眼中,依旧是寒门。
他自幼好学,才华横溢,在家乡多有闻名,第一次参加科举,竟名落孙山。李振不服气,又连着考了几次,仍是榜上无名。
在这个过程中,他也逐渐意识到
很多东西,和真才实学没关系。
也因此变得愈加愤世嫉俗,可以说,对于黄巢大军的到来
他心中虽然也有惊惶,但未必没有幸灾乐祸。
“不过,这十万大军,看似汹汹,但只眼下长安城外这一幕,便是没有半分胜算!”"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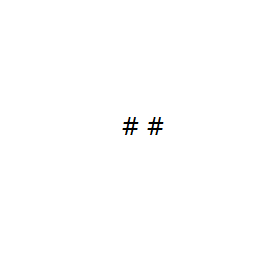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